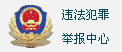圖為彭偉棟近照。
日前,中國作家協會公布2022年新會員名單,我市作家、本報記者彭偉棟位列其中,成為我市最年輕的中國作協會員。近日,記者對他進行了采訪。
播下文學種子
正所謂“讀寫不分家”。對作家而言,讀書是打基礎。
彭偉棟的父親生前十分愛讀書,收藏了《唐詩三百首》等書。其父教幼年彭偉棟讀唐詩,一字一句,抑揚頓挫。久而久之,他受到傳統文化的熏陶,逐漸愛上讀書了。十多歲的彭偉棟為了買到好書,經常穿梭在陸城馬街的書店,購買名著、雜志等。讀書百遍其義自見。每次讀后,他都有一番新的體會,當時他讀《西游記》,認識到人生在世活著不容易,很多人都走在“取經路上”,必須以積極樂觀的態度勇往直前,克服人生困難。后來,愛書如狂的彭偉棟覺得書太貴了,就專門從舊書攤買《鏡花緣》、《詩經》、《古今奇觀》等書,每次得到好書都愛不釋手。他廣泛的閱讀使自己開拓了視野,感受到文字之美。
彭偉棟讀中學時,他的語文老師是個文學愛好者,每次上課總會帶幾本《雜文選刊》《雜文月刊》過來,時常與學生談雜文寫作、熱點時事,并在課余總會將自己買的雜志借給學生閱讀。彭偉棟看了這些雜志,大受啟發——那些雜文作者寫的是“身邊事”,雖然針砭時弊,但愛之深責之切,展現的是濃濃的愛意。從此,彭偉棟愛上了雜文,他購買每年的《中國雜文年選》,認為好的雜文是“見血”的、能干預現實的,字里行間呈現著人文關懷。
愛讀雜文,便萌生了寫作欲望。彭偉棟在中學時期開始嘗試寫雜文,記得當時在《汕尾日報?教育周刊》上發表第一篇雜文《貶牛論》,寫牛有奴性,只會埋頭苦干而不知有獨立思想,借此譏諷某些人頭腦里的封建思想。文章寫得幼稚了些,但是發表后卻給他更多創作動力。彭偉棟在讀高三時,寫了一篇題為《我是英雄》的雜感,講年輕的自己要有自信,要當生活中的“英雄”,要敢于講理想信念、敢于獨立思考、敢于質疑權威,字里行間激蕩著一股青春氣息。可是后來被語文老師判為不合格。彭偉棟當時不服,投稿參與了《作文》雜志主辦的“文心杯”全國中學師生作文大賽,幾個月后主辦單位寄來三等獎獲獎證書,他頓時歡呼雀躍,心想:老師的“作文指向”未必就是金科玉律,文學的世界需要不斷探索。
走上社會后,彭偉棟在陸豐的民辦學校教了幾年書,在此期間寫作一發不可收拾,先后寫了《做名狐貍》《流行色》《想起劉文典的“月光課”》等大量的雜文。因為身在教壇,關注教育,當在書中讀到沈從文、劉文典、蔡元培等民國大師的教學軼事后,不禁心潮澎湃,寫了20多篇“民國大師啟示錄”系列雜文,陸續在省、市報刊發表,有的甚至被省級雜志轉載。后來,因為他越寫越有影響力,收到《汕尾日報?教育周刊》編輯的約稿來電,他當即答應。當年教師節前夕,他在該報開辟了個人雜文專欄“節前節后花磚錄”,發表了一系列有關教育的雜文,受到讀者的關注。當時,有人稱剛出道的彭偉棟為“雜文新秀”。
創作成績斐然
彭偉棟崇尚曹雪芹和魯迅,認為好作品必須具有人文關懷,呈現對現實人生的思索。
他發表在《今晚報》的散文《小書房大世界》里說:“書房窗外,也別有風景:一棵青翠的竹子,雖然略顯孤單,卻挺拔有力。我在讀書時,聽到竹葉隨風搖曳的沙沙聲,總會想起鄭板橋的詩: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這里并非‘衙齋’,但讀書人總要關心人間疾苦,講點理想情懷,文章要關乎痛癢,少寫些風花雪月。”這正是彭偉棟的文學創作觀念!
近年來,彭偉棟在《百家講壇》《南都周刊》《廣東教育》《今晚報》《羊城晚報》《中國改革報》《現代教育報》等報刊發表600多篇雜文、隨筆。其中,“《鏡花緣》異事”系列雜文和“尋食錄”系列隨筆在《今晚報》“今晚副刊”分別連載。有多篇作品被《各界》《晚報文萃》《讀書文摘》《經典雜文》《政府法制》等雜志轉載和入選《中國雜文年選》、《似是故人乘風來:在四大名著中遇見你我他》《1小時讀名著》《嶺南文藝百家叢書之翰墨匠心》等文學選本。多次獲得全國、省級文學賽事獎項,《豬八戒的隱權力》在《百家講壇》發表后被該雜志評為“最受讀者歡迎的文章之一”。出版隨筆集《水滸掠影》《神仙妖怪的另類臉譜——〈西游記〉的江湖》。
出版第一本書
出版處女作,對作家而言非常重要。彭偉棟出的第一本書是《水滸掠影》。
彭偉棟從小愛讀《水滸傳》。他說,“每個階段讀《水滸傳》總有不同感受。長大一點讀,才認識梁山好漢并非全是真好漢,更多的是嗜血的流氓。”于是,他花了近兩年對《水滸傳》進行研讀和寫作,走近了人物的內心世界,解讀出他們反人性的一面。他希望讀者能從自己的文章中讀出“痛感”,做分清善惡、辨別是非的明白人。他的“水滸掠影”系列文章在多家省、市刊物上發表,其中《東岸》雜志專門開辟了專欄發表這組系列文章,受到了一些好評。
彭偉棟說,“我寫解讀《水滸傳》的文章,側重讀者忽略的小說細節,例如打虎英雄武松愛性騷擾女性、在監獄大搞潛規則的戴宗是守財奴、盧俊義經常反人性打罵管家李固才導致他加害自己等,讀者讀了這些文字,會發現這哪里是真好漢所為?與他們標榜的‘替天行道’方針根本背道而馳!”
2018年,彭偉棟將自己寫的50多篇“水滸掠影”系列文章結集出版,一時之間好評如潮。知名學者吳鉤寫給該書的推薦語是:“施耐庵的《水滸傳》自問世以來,誕生了許多衍生的作品,比較著名的有薩孟武先生的《水滸傳與中國社會》,王學泰先生的《‘水滸’識小錄》,虞云國先生的《水滸亂彈》。我的朋友‘十年砍柴’也是以創作《閑看水滸》而成名于網絡。現在,彭偉棟也寫出了一本《水滸掠影》,以輕松活潑的筆調,劍走偏鋒的視角,重新解讀《水滸傳》的人物與故事,以觀照世道人心。倒也別開生面。”著名雜文家羅青山在讀完《水滸掠影》后,特意致信彭偉棟說:“大著另辟蹊徑,以獨特的視角系統地分門別類地去解讀《水滸傳》人物、事件,為邊緣人物鳴冤叫屈,揭穿道貌岸然的人物的假面具,以及梁山在忠義旗號掩蓋下的重重黑幕等。每個篇章從表面上看并沒有聯系現實,但其中大部分都有暗諷和隱喻,不是為顛覆而顛覆,為翻案而翻案。梁山形形色色的人物并沒有死,仍活在當下。這就是大著的現實意義,也是它成功的地方。”
選擇解讀背后
2019年,彭偉棟出版了第二本書《神仙妖怪的另類臉譜——〈西游記〉的江湖》,借解讀《西游記》的神仙和妖怪批判社會不良現象。在此之前,他的很多解讀名著系列文章在知名的雜志《百家講壇》發表,有時與閆紅、六神磊磊等名家在同期雜志“同臺亮相”。
對四大名著談論的人甚多,為什么彭偉棟還要選擇以此作為創作方向?彭偉棟說,“其實,四大名著之所以經久不衰,是因為有很強的文學魅力,通過描繪出氣象萬千的人間或神魔世界,展示了人性之美和人性之惡。可以說,我們是可以在四大名著里讀懂歷史的,因此值得一講再講,溫故而知新。我喜歡通過現象看本質,不管解讀《水滸傳》還是《西游記》,都立足于不僅放在解讀原著層面,還往深里挖,延伸出現實意義。例如我寫解讀《西游記》時,說二郎神之所以傲氣十足、目中無人是因為‘上面有人’;很少出場的哮天犬其實并不差勁,他安守本分,盡忠職守,沒有私自下凡禍害人間,是《西游記》中‘不合時宜’的異類,值得點贊。我在字里行間追求的是人間公道,相信引起了很多讀者的共鳴。文字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我一直在努力!”
在新的起跑線
當記者提及加入中國作協后有何感受時,彭偉棟十分嚴肅地說:“我認為,加入中國作協既是榮譽,也是鞭策!我站在新的起點上,要以此為動力,努力寫出更好的文學作品!”
彭偉棟還說,“曹丕在《典論》中說,‘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進行文學創作如同在走朝圣之路,要守得住寂寞,甘坐冷板凳。一個作家,即使做不到曹雪芹‘批閱十載,增刪五次’那樣,也應該寫好放一放再推敲,要對得起自己也要讀得起讀者。年歲漸長,我更是如履薄冰,努力寫好文章的每個字。這十多年來,每當夜深人靜,只要有空,我不是在讀書就是在寫作,充電與創作是密不可分的。路還好長,不能懈怠!”
提及下來的創作計劃,彭偉棟興致勃勃地說,“記得作家汪曾祺寫過散文《吃食和文學》,他從美食中延伸出更多現實意義,呈現出對文學創作理性的思考,使我在文學創作上受到啟示——寫小小的美食原來也可以有大主題、大思想!于是,我漸漸對海陸豐的美食有了更大的興趣,認為也可以寫寫。我下了一番苦功,走上路邊專注看別人怎么做美食、詢問上一代人對美食的認識、思考海陸豐特色美食如何傳承等,然后大膽動筆來寫。我從去年到目前寫了51篇‘尋食錄’系列文章,想以生動的筆墨寫從美食的制作、口味等聯系到飲食文化的傳承、文學創作的技巧、人生理想信念之類的宏大主題,讓讀者讀我的文章收獲更多。這組文章有的在《今晚報》‘今晚副刊’連載,有的在《羊城晚報》“花地”副刊發表,還有的被《淮南日報》等報刊轉載,有了點影響。今年內準備將這組文章寫完!我明年初步打算寫個‘身邊人掃描’系列隨筆,寫寫身邊的朋友、親人的軼事,展示他們的思想靈魂。正所謂‘文學是人學’,從這方面說寫這個也許更有意義!”
彭偉棟最后說,“只有勇攀高峰,才能看到更美的風景。在此感謝鼓勵我寫作的師友,是他們一路的鞭策才有我今天的堅持!”
汕尾日報記者 沈綠洋






 粵公網安備 44150202000069號
粵公網安備 44150202000069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