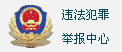大型音樂劇《少年彭士祿》劇情簡介:

《少年彭士祿》劇照
第一場:血雨腥風。1928年二月底,紅軍和赤衛隊為保衛蘇維埃與敵人進行生死搏斗。在彭湃的白樓前,周鳳率全家轉移,把年僅三歲的孫子士祿交給奶媽。不久彭湃的愛人蔡素屏被敵人押往刑場……。
第二場:韓江遇險。1931年夏天,國民黨瘋狂追殺彭湃的遺孤,黨中央命令東江特委將彭士祿護送到江西瑞金。彭士祿被彭述帶到潮安。他在林甦的護送下,由潮安乘船從韓江溯江而上至豐順的留隍鎮時遭到敵軍的攔截,林甦等犧牲。彭士祿在船夫掩護下回到潮安彩塘村,在這里吃百家飯穿百家衣,村婦潘舜貞更是對彭士祿百般呵護。1933年8月由于出現叛徒,彭土祿和潘舜貞、山頂阿媽等被捕。
第三場、獲中溫情。在潮州監獄,潘舜貞等與八歲的彭士祿相依為命。后來被捕入獄的紅軍戰士小花,告訴彭士祿其父母六位親人為革命犧牲的家史,并鼓勵他堅守先輩的共產主義信仰。
第四場、重見天日。1935年,彭士祿從廣州感化院被釋放出獄,他一路討飯走了半年回到潮安,在土地廟前與討飯流浪的山頂阿媽相遇。1936年,共產黨通過潮安的上層關系,導演了一場法庭認親,彭士祿為了留下來照顧潘舜貞,竟然不認親祖母周鳳,在潘舜貞的開導下終于婆孫團圓。
尾聲:1940年,歷經千辛萬苦的彭士祿終于被黨組織送至延安,青年干部學院的教師帶領學生熱烈歡迎他的到來。彭士祿要求奔向抗日的戰場,老師鼓勵他要傳承父輩的精神,為中華民族的解放和偉大復興而努力學習。至此,全劇到達高潮。
該劇以彭士祿從一個尋親的幼童成長為一名革命戰士的經歷為明線,以黨中央、地方黨組織極力保護彭湃烈士遺孤為暗線,不僅表現了彭湃烈士的妻子蔡素屏刑場囑咐兒子為中華民族的解放貢獻力量的英雄壯舉,同時還著力表現了以林甦、潘舜貞為代表的海陸豐和潮汕地區的黨員群眾聽黨話跟黨走、舍己護孤的感人情懷。全劇音樂和唱詞優美,既波瀾起伏又高潮迭起,演員在故事情節的感召下把演技發揮得淋漓盡致,不失為難得的一部紅色經典劇目,是紀念建黨一百周年的經典之作。 (汕紅)
《少年彭士祿》誕生意義重大
○ 李志煌
觀看了紅色經典大型音樂劇《少年彭士祿》的首演,演出非常成功。今天參加有關本劇的專題交流討論,感到心潮澎湃、榮幸之至。
彭士祿院士是一位集老革命、大科學家、高級領導干部于一身的傳奇人物:他是革命英烈彭湃的優秀兒子、是中國核潛艇首任總師、是首批當選的工程院院士,也是我國核動力事業的開拓者和奠基人。彭老從烈士遺孤到杰出的科學家,捐獻了全部巨額獎金,踐行著“感恩、立志、報國、敬業、無私、奉獻”的理想信念,經歷風霜雪雨依然信念堅定、鐵骨錚錚、勇攀高峰,用實際行動詮釋了共產黨員的“不忘初心 牢記使命”,堪稱我們民族的脊梁!
首演的《少年彭士祿》,真切地再現了彭士祿4歲成為孤兒、先后兩次被捕入獄、14歲參加革命等一系列苦難而堅強的經歷,展現了彭士祿姓百家姓、穿百家衣、吃百家飯長大的生動場景。音樂劇以新穎多元的內容形式,演繹出一幅壯闊豪邁的革命圖景,讓我們對少年彭士祿的心路歷程有了全景式的認識,也讓我們看到,正是這片老一輩革命家先后涌現、千萬優秀兒女拋頭顱灑熱血的南粵大地,才孕育出彭士祿這樣年少有成、頂天立地的國之棟梁。作為老一輩核工業人的優秀代表,彭士祿常常講,他一生只做了兩件事:一是造核潛艇,二是建核電站。彭老舉重若輕,卻為我國核動力事業從無到有作出了極端重要的貢獻,是核工業精神的集大成者。
不久前,中核集團黨組發出了向彭士祿同志學習的號召,黨組成員在專題讀書班上帶頭學,系統內廣大黨員讀《彭士祿傳》、看《我的父親彭士祿》專題片、走入彭士祿故居、組織事跡宣講,在全集團掀起學習彭士祿同志先進事跡的熱潮,在學習中緬懷可親、可愛、可敬的核工業老前輩,致敬中國核動力事業的“拓荒牛”。在建黨100周年這樣一個特殊歷史時期,《少年彭士祿》的誕生意義重大。這部音樂劇首開少年彭士祿文藝作品的先河,是彭士祿精神研究的思想邏輯和歷史邏輯的起點,對于中核集團深入學習彭士祿同志先進事跡,以系統思維在黨史學習教育中突出核工業特色,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和借鑒意義。期待繼續擴大作品的影響。我們也將一如既往地支持以彭士祿為代表的核工業精神研究,鼓勵產出富有影響力的文化成果,以優異成績為建黨100周年獻禮。
(作者為深圳中核集團黨委書記 董事長)
紅色歷史的重新觀照與大眾趣味的融通
——評紅色音樂劇《少年彭士祿》
○ 龍其林
2021年5月22日,紅色音樂劇《少年彭士祿》的首演在汕尾市馬思聰藝術中心舉行,這距離1922年7月29日全國第一個農民協會——六人農會在海陸豐的成立、距離1927年11月中國第一個紅色政權——海陸豐蘇維埃政府的建立,將近一個世紀了。彭湃這個名字在很多青少年甚至成年人的記憶里,已經被和平、快樂的生活漸漸取代了。而《少年彭士祿》的演出,則將近一個世紀之前發生在海陸豐地區的紅色革命歲月重新拉回到人們的眼前,讓大家在盛世中重新回到崢嶸的革命歲月,感受那敢為人先、無私奉獻的海豐精神。彭湃被毛澤東稱之為“農民運動大王”,其子彭士祿又是共和國第一代核潛艇的總設計師與核動力專家,他們的人生本就具有傳奇色彩。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的重要年份,重新回顧艱苦奮斗的革命歷程,發掘共產黨人與人民群眾的魚水深情,領會共產黨員的本色與初心,展現共產黨員的使命擔當,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少年彭士祿》的價值不僅在于選題具有重要意義,演出時間具有紀念意義,它還具有更多的可以值得肯定之處。
首先,這部音樂劇是對國內紅色音樂劇的延續與發展。20世紀60年代《紅色娘子軍》被搬上大熒幕及改編為紅色芭蕾舞劇、紅色現代京劇、紅色漢劇,之后“八個樣板戲”紅極一時,但此后紅色音樂劇的創作及演出日漸減少。《少年彭士祿》不僅是汕尾市首部原創紅色音樂劇,而且也是新世紀之后國內紅色音樂劇的新收獲。
這部劇作努力探索紅色題材與音樂、歌唱、舞蹈的現代化融合,努力探索嚴肅革命題材與大眾審美趣味之間的協調,力圖用音樂劇、歌舞劇的方式來拓展紅色題材作品的審美空間,這種探索具有創新意義。它在繼承紅色經典劇作的表演程式上,大膽創新,拓展了紅色歌舞劇的表演動作語匯。如少年彭士祿在母親蔡素屏英勇就義后,在鄉間田野中的唱段逼真地刻畫了失去母親后的孩童的傷痛與絕望,小演員的表演很生動傳神,用了中國傳統戲劇表演中很少使用的直抒胸臆的歌唱及動作進行表現。同時,這部音樂劇還將現代音響設備與各類樂器混合編排的伴奏方式進行融合,不僅起到了伴唱的作用,而且也恰到好處地反映了彭士祿及周鳳、山頂阿媽、潘媽媽等眾多人物的身份及精神狀態。
其次,這部劇作對紅色主題的傳達采取了一種柔和的、富于人性溫度的傳達。這部劇作不停留于政治概念的宣傳,而是通過革命領袖、革命戰士、人民群眾對于烈士遺孤的關愛,來表現出共產黨人的博大胸懷與濃厚的革命情誼。無論是為了掩護彭士祿而犧牲的林甦等東江特委的負責人、戰士,還是為報答共產黨和彭湃恩情的山頂阿媽、潘媽媽等人,都散發著一種濃烈的人情味。革命斗爭不再只呈現出冷酷無情的敵我斗爭場景,而且也將革命領袖的關懷、紅軍戰士的柔情、普通民眾的感恩等人間情誼展現得淋漓盡致。從這個意義上說,這部音樂劇不僅僅是一部紅色題材的劇作,也是一部充滿人情味、展現人性美、弘揚人的頑強生命意志的劇作。
第三, 這部音樂劇具有濃郁的嶺南文化特色。當代的話語、音樂劇越來越趨于同質化的形式下,《少年彭士祿》則注重彰顯潮汕地方文化,表現出一種鮮明的地方特色。在中國的文化密碼里,自然的、地理的、空間的存在常常會滲透、轉化為社會的風氣,進而影響民眾的個性、氣質與心理。在劇作中,潮汕的山水、建筑、習俗傳達了一種潮汕尤其是海豐民眾的質樸、勇敢、重義的氣質。中國的第一個農會、紅色蘇維埃政權在汕尾建立,也許并不只是一種偶然,它與地方上的文化氣質、社會心理息息相關。
當然,這部劇作也有可以繼續完善的地方。該劇的主題是《少年彭士祿》,劇作結尾時延安青年干部學院的教師歡迎彭士祿并鼓勵他好好學習,隨后演出結束,屏幕上出現一段文字,簡單地交代了彭士祿后來的經歷。《少年彭士祿》所表現的主人公的坎坷經歷,對于后來彭士祿的成長及為共和國強大所做的貢獻有什么關聯?這一點在劇作中語焉不詳。如果能夠適當地交代一下早年的逃亡、牢獄生活對其后來的影響,那么劇作的主題會更加凸顯。
(作者系廣州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廣州市黃埔區作家協會副主席)
紅色革命精神在海陸豐大地薪火相傳
——評大型紅色題材音樂劇《少年彭士祿》
○ 何牧人
《少年彭士祿》音樂劇于2021年5月22日在汕尾市馬思聰藝術中心正式演出,這部劇在建黨一百周年之際推出可謂恰逢其時,其有以下幾個方面特點值得關注:
一是選題好,注重共產黨、紅軍與人民群眾的魚水相依的關系。目前紅色文學需要新鮮的主題和題材,在新中國成立初的紅色劇本如《智取威虎山》《白毛女》《劉胡蘭》《小兵張嘎》等主要是講革命者、革命群眾和國民黨、地主富豪、土匪、日寇的斗爭,強調敵我矛盾,體現出解放軍、人民群眾的智慧。《少年彭士祿》則以革命遺孤彭湃之子彭士祿在人民群眾和紅軍保護下如何逃脫國民黨追殺不斷健康成長確立革命理想為民族和國家事業奮斗的過程,它體現了革命者與人民群眾的魚水關系,人民群眾是水,革命者和紅軍是水中的魚,水養育了魚,魚離不開水。紅色革命遺孤就在人民群眾的保護下,成長為國家的棟梁之才。
二是從彭湃與彭士祿的父子關系入手,表現了人民群眾對革命領導人的愛戴,以及為保護革命遺孤、保護革命火種而不怕犧牲的精神。海陸豐農民運動領袖彭湃有幾個第一,第一個發起農會運動,第一個建立革命根據地,第一個建立紅色蘇維埃政權,第一個頒布土地法,毛主席稱贊彭湃是農民運動大王,周恩來也說過彭湃的根據地影響很大。彭士祿作為彭湃的兒子,很好地繼承了父親彭湃的革命理想。《少年彭士祿》是可謂書寫革命遺孤題材的第一個新的劇本,彭士祿是科學家、核動力潛艇的總設計師、紅色革命遺孤,這幾重身份都讓彭士祿非常值得大寫特寫。今年3月份,彭士祿去世,享年96歲,古人說蓋棺定論,這個定論當然有來自于中央、廣東、汕尾各級政府的官方認可,但同樣重要的是文藝作品對于彭士祿精神弘揚和書寫。今年又是建黨100周年,羅如洪先生創作的《少年彭士祿》,可謂是適逢其時的重要文藝作品。
三是具有廣東地方色彩的紅色革命精神的發掘。在建黨100周年之際,以前相對重視不夠的彭湃建立紅色革命根據地的價值和意義開始得到凸顯,這個原因我們可以略作說明,1978年改革開放開始弱化紅色革命文化,強調經濟發展,紅色文化未曾得到重視,比如彭湃故居目前還只是省級文物保護單位,這其實都是重視不夠的體現。這部劇較好地體現了地方色彩的特殊性和整個紅色文化的民族精神和國際主義精神,這是一個較大的優點。
四是情感、唱詞、音樂、場景、動作的完美結合。情感是既堅強又柔弱,唱詞優美,古典的韻味,革命的斗爭,現代的生活結合得很好,音樂也很美,這是一部史詩性的音樂劇,將革命戰爭和個體情感都進行了藝術化的表達。整體來說,這是一部優秀的紅色文學作品,海陸豐紅色革命精神,由彭湃所確立,在人民群眾保護革命遺孤彭士祿的這樣一個薪火相傳中,得到承傳。這種革命精神在當代的寫作,也將與廣東和中國的改革開放相結合,成長為一種新的奮發有為、積極進取的精神,并將激勵著廣東人在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推動中國經濟文化發展中繼續努力。
(作者筆名何牧人,文學博士,廣東外語外貿大學中文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
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好
—— 觀《少年彭士祿》有感
○ 黎保榮
對于音樂劇《少年彭士祿》,我接觸過三次:第一次是閱讀羅如洪發表在《戲劇之家》2018年第31期的《少年彭士祿》,后兩次是在今年5月21、22日晚觀看了同名音樂劇的彩排與首演。客觀而言,該劇具有如下特色。
一、 音樂劇的形式與內容。該劇大概有8首歌;形式上有獨唱,合唱。如蔡素屏、彭士祿、姑媽、山頂阿媽、小花等人都有獨唱。內容有悲歌、壯歌與歡歌。就悲歌而言,如蔡素屏對兒子彭士祿的不舍之歌。就壯歌而言,如蔡素屏對同志們的鼓舞之歌。就歡歌而言,如彭士祿的“潮汕處處是我家,大家把我來牽掛。姐姐送我新衣裳,哥哥教我學文化。一人任吃百家飯,戶戶都留我口糧,一人獨占百家姓,村村祈福我沾光。千家門神來保佑,我如魚兒得水——樂哈哈!”可謂歡聲笑語。而在表演上,可謂聲情并茂,動作到位,角色選擇合理,布景、燈光、音效、舞蹈等都比較搭配。
二、 文史相生、失事求似在“文史相生”方面,是文學與歷史的相生,一句話就是共產黨的大歷史與彭士祿的小歷史相結合。就大歷史而言,如農民運動,共產黨入獄現象,紅軍,蘇維埃,周恩來,信仰。就小歷史來說,如彭士祿的三歲喪母、四歲喪父,成為孤兒;共產黨遺孤與群眾的魚水情;8歲和11歲兩次入獄;后到香港、澳門、延安。獄中有一個傳燈的細節,象征著做彭湃與共產黨精神的傳燈人,具有薪火相傳的象征意味。與此類似,劇中不少細節都比較細膩。孤兒不孤及其原因也值得探討。彭士祿可謂孤兒不孤,他吃百家飯長大,有幾十個媽媽(姑媽、山頂阿媽)和爸爸。而之所以那么多農民和革命者愛護他,是因為他們受過彭湃的恩,以此報恩。彭湃的大愛,激發了農民和革命者的大愛(彭湃曾經幫助過農民,是革命者的戰友或領袖)。這也是共產黨的信仰與愛在起作用。當然該劇也有虛構的地方,對于歷史劇來說,這是很正常的。就像郭沫若曾經認為歷史劇不妨“失事求似”,換言之史實可以有出入,但是保持精神的相似性。例如該劇虛構了小花這個兒童團長和小紅軍,以及監獄中的教書先生。但是從歷史來看,1936年祖母周鳳千辛萬苦找到彭士祿,并且通過陳卓凡設法將他營救出獄,將他帶到澳門。所以法庭認親那幕戲,不如改為在阿媽家里認親,一是為了劇情集中、有力,以免枝節過多;二是表現彭士祿在血緣親情與非血緣親情之間的心理糾結,以此探尋人物豐富的內心世界。劇本對“少年”特征的描寫還是比較到位的,同時彰顯了這是一位不平凡的少年。彭士祿在監獄中那場體現了他的成長(對信仰的確認,對長大的自信),出獄流浪那場體現了他生命力的頑強,尾聲體現了他的堅定、樂觀,體現了共產黨不僅有對他的保護,也有對他的培養。
三、 故事敘述的地方路徑。劇中表現了潮汕或汕尾的事物:蓮花山、韓江、潮汕平原;龍津水、紅棉花、紅場、白樓、土地廟、潮汕農村、潮汕建筑;方言。同時,該劇把這些事物放置于海豐、潮安、汕頭、廣州、澳門、香港、延安等不同的空間里,更顯示出潮汕或汕尾景物的獨特。地方路徑與地方色彩不一樣,后者主要是風土人情層面的,前者除此之外,還突出了地方與中心的比較視野,路徑表明了這是一種明確的道路追求,是一種與中心相對的有價值、有特色的空間。
四、兩種革命精神。該劇體現了兩種革命(政治革命與科學革命),也體現了兩種革命精神。在此意義上,該劇多次提到讓彭士祿好好讀書,學好科學文化,好建設新中國。其實讀書不僅成為了一種革命道路,也暗示了潮汕人對讀書的尊重。但是,我忽然想提出一種假設:假如彭湃甘心做大少爺,不參加革命,很可能就不會有如今的彭士祿,因為他即使讀書,可能也出國了,也許不會接受國家任務,不會有那么強烈的革命情懷與家國情懷。總之,該劇是將音樂與表演,歷史與文學,革命與鄉土結合得比較好的作品,值得關注。
(作者為肇慶學院文學院教授,肇慶市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






 粵公網安備 44150202000069號
粵公網安備 44150202000069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