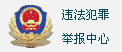○郝子奇
失雪的玉龍山
沒有人看到。
什么樣的手摘走了山頂上數千年不肯融化的雪。
現在。沒有人看到雪。
我站在無雪的山峰下。一團團粘連的云霧正在起身。它們需要風的拉動,以擺脫山的蒼老。
蒼老。是那只手嗎
那些被時光風化的白斑,在高高的山的肉體上,裸露。
雪一樣蒼白。不是雪。
雪。是山的歷史。
一只手,如何改變著歷史。它撫摸的巖石已經長出了皺紋。只有可以輪回的小草,還是去年的樣子,在重復中,躲過了那只改變的手。
而那只手,看不見它伸出來,已取走了悲壯的雪。
那只取走了雪的手,又在摘取著什么
云朵已經低于山巒。閃電正把雷聲放進峽谷。
失去雪,峽谷裂縫越來越寬。去年等食的小鳥,翅膀已經硬了。它們振動著羽毛,飛到了云的高度。
(多年前,我帶著青春踏雪而上。現在。在山下,在沉淀著云朵的湖水里,我復制了自己,卻被那只無形的手,抽走了力量和青春。浮在水面的疲憊,仿佛蒼老的山脈,沉默。)
起風了。
在飛渡的云團里,我看見了隱匿的手形。
像剝取棉花一樣,取走了云朵里的骨頭。
而我無法打撈被它取走的青春,帶著蒼老的影子遠離了無雪的山。在古老的客棧,獨自傾杯,由于看到夕陽從指縫漏下,不能握住最后的光,等待著夜晚像失去的雪一樣來臨。
古趙國長城
一坡野草。未黃,站在歲月的高處,仍是千年不變的模樣。
它們舉著手,遮住了坍塌的亂石。那些無法站直的歷史,有著戰國時的亂象。
一脈陽光,穿透野草的手。亂石上,這些小小手掌的斑駁,仿佛滄桑漏下的沙粒。模糊。殘缺。
多么久遠的陽光。照過的戰旗,已被歷史的烈烈風暴撕碎,散在一些角落。照過的那些沖鋒的戰士,已走過長城的缺口,沒有回頭,也沒有走回出發的故鄉。
沒有躍過長城的戰馬,在峽谷里撕鳴。戰爭的鞭子,抽在汗水濕透的脊背上,有血,有散落的鬃毛。
已經升高的狼煙,看到了滿弓的長箭,在堅硬的城墻上,撞出了一個又一個的斑點。
一段圍墻,擋住侵略和戰爭,這是很久的歷史了。
真正的戰爭,起于人心。
如果人心長出了侵略的翅膀,一段墻,如何擋得住翅膀扇動的風暴。
修墻的人,終被打開城墻的人所征服。
放不下屠刀的人,終被歷史所斬殺。
歲月漫長。和平,是柔軟和溫暖的渴望。像現在的陽光,照看這些被戰爭打磨的石頭,像母親心疼地撫摸著殘疾的孩子。
千年之后,所有的都被野草掩蔽著。
我們撥開了野草,無法撥開歷史的真象。
凄迷的野花,是深秋最后的燦爛。再漫長的歷史,也無法摘盡一坡野花,它們有著生生不息的頑強和努力。
野花叢中的我們也是。
歷史深處,我們的祖先,搬著一塊塊石頭,為子孫壘著和平和幸福。
現在,我們坐在這些留著祖先手印的石塊上,看著山河起伏,到處是人間煙火和幸福的生活。
這是多么不息的繼續。
遙遠的將來。仍會有一雙手,摘下不敗的野花,在古老的石頭上,像我,無限地念懷。
無限地向往。
金山寺
淇水,沒有斷橋。那只敲開許家溝柴門的纖纖素手,應該涉水而來,牽著樸實的后生,他們一塊在金山寺,聆聽了誦經的風暴。
斷橋是后來的人修筑的。
歷史出現了裂口,愛情如何彌合這漫長的傷。
金山寺下。淇水干凈。
岸邊。延綿的竹林,足以安放等待千年的纏綿。大風吹飽的谷穗,足以喂養人間的愛情。這時候,只需要男耕女織,就是幸福。
我來。已找不到宋時的門環,去驗證一場愛情的悲歡。
那時候,風動云低,衣袂飄飄,纖弱的白素貞,抱定萬劫不復的決心,敲開金山寺的大門,人性的淇水,在她的身后上漲,洶涌澎湃。
那場傳說中的大水,已退卻多年。
那些被洗白的巖石,只剩下滄桑的苔斑。它們的沉默,讓一場刻骨的見證,成為了秘密。
復活的野草上,開著白色的菊花,一只又一只螞蚱,在現代陽光下,振動著翅膀。
寺院深深。沒有了法海。
沒有了白素貞。也沒有了許仙。
仿佛,一場大水之后,人妖在愛情的奔跑中同途,走到了西湖,再沒回來。
多少年,一切都在歷史中老去。
只有不朽的愛情,在不息的淇水邊站著,如初。
【名家簡介】郝子奇,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詩歌學會理事,河南散文詩學會副會長,鶴壁市作家協會名譽主席。作品散見全國報刊,入選多種年度詩歌年度散文詩等選本,多次獲獎。出版散文詩集《寂寞的風景》、《悲情城市》、《河南散文詩九家》(合著),詩歌集《星空下的男人》。






 粵公網安備 44150202000069號
粵公網安備 44150202000069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