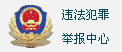○趙子清
人的一生中,總有一些歲月會在記憶里留下深刻的烙印。對我而言,1979年8月至1980年7月,是真正決定人生命運的一年。那一年,我成為江西省尋烏中學高二(6)班——全校唯一的文科畢業班中的一員,與六十位同學一起,向高考這個人生大關發起沖刺。后來才知道,1980年江西省高考錄取率僅為百分之五,我們正如千軍萬馬爭過獨木橋。
高二(6)班上的同學來自全縣各地:有像我一樣的應屆生,有復讀多年的往屆生,還有十幾名文體特長生。班主任徐生昌老師讓我當了班長,他待人溫和,做事干練。開學第一次班會上,他看著我們這些從全縣各地匯集而來的學生,用當年考上北京大學法律系的林翰章學長為例,語重心長地說:“知識改變命運,成就全靠自己。這一年,將決定你們的人生走向。”
師者仁心
1979年暑假,學校組織了高考補習班。我提前一周來到縣城,住進徐老師家中。他家住在中山窩的老磚房里,兩間屋子擠著一家四口。我和徐老師睡在同一張木板床上,每晚都能聽到他勞累一天后均勻的呼吸聲。白天,他在臥室兼書房里給我開小灶,單獨輔導歷史;晚上,我借著昏黃的燈光復習,他則在桌前準備講義,燈光的光暈映照著他專注的側臉。
最難忘的是那個雨夜。晚飯后,徐老師說要帶我去看日本電影《追捕》。外面下著傾盆大雨,我們只有一把舊傘。他把傘幾乎全都傾向我這邊,自己的半邊身子都淋濕了。我們在泥濘的小路深一腳淺一腳地走了半個多小時,終于趕上了最后一場電影。回去的路上,他給我講電影的背景,也說起自己早年艱難的求學經歷,完全忘了渾身濕透的衣裳。那一刻,我深深感受到了老師無私的關愛。
寒窗苦讀
我們高二(6)班的教室設在縣中老校舍的二層,木質樓板走起來咯吱作響。男生宿舍由舊倉庫改建,五十多人同住一個大房間,每個人的床鋪剛好夠平躺。遇到下雨時,屋頂常常漏雨,大家不得不用臉盆、飯盆接水。夜深人靜時,叮叮咚咚的滴水聲反而成了苦中有趣的回憶。雖然條件艱苦,但每個同學都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常常挑燈夜讀到深夜。
學校對我們這個唯一的文科畢業班極為重視。藍波副校長親自教政治課,他講課深入淺出,把枯燥的政治經濟學原理與生活實際相結合,講得生動有趣。徐生昌老師負責歷史課,經常熬夜用鐵筆在蠟紙上刻寫復習題,第二天帶著滿手油墨來上課,發下來的油印資料還散發著淡淡的墨香。數學彭佛冶老師講課細致入微,總是留意學生的反應。他有個習慣,講到關鍵處總會看看我,只要我眼神里還有疑惑,沒有點頭表示懂了,他就絕不輕易翻過去,總是換個角度再講一遍。這份無聲的關照,讓我既感到壓力,又充滿感激。
面對繁重的學業,我摸索出了一套適合自己的學習方法。每天下午四點半下課后,我常常獨自爬到學校后山,找一棵枝葉茂盛的大樹坐下復習。那里視野開闊,可以看見整個縣城和遠處的田野,登高望遠,心中的壓抑和疲憊頓時消散不少。我將政治、歷史、地理等需要大量記憶的科目內容提煉出核心要點,再由主干逐步展開細節,像繪制一棵“知識樹”。比如一章歷史內容,我先歸納出三五個核心觀點作為主干,然后將相關的年代、事件、意義等關鍵細節分門別類地填充進去。這個方法幫助我建立起清晰的知識體系,學習事半功倍。
手足情深
那年,我的大哥趙敏陽也來到尋烏中學理科班補習。他1978年高中畢業,在農村務農后到學校“回爐”。我們兄弟倆同住在那個由舊倉庫改成的大宿舍里,擠在一張窄窄的木板床上。吃飯時,我們用一個搪瓷大盆裝上淘好的米,送到食堂的大蒸籠里去蒸。菜就是家里帶來的咸菜、豆豉,偶爾打一份食堂最便宜的素菜分著吃。大哥學習基礎不好,但特別刻苦,常常看書熬到深夜。功夫不負有心人,他補習二年后考取了浙江冶金經濟專科學校。
迎接高考
1980年7月7日,高考終于來臨。考場設在母校尋烏中學。記得語文作文題目是《達芬奇畫蛋有感》,我寫得格外順暢。其他科目也考得還好。只是數學考試時,我因為看錯一道大題的要求而失分,走出考場時心情沉重。
七月流火,高考成績放榜了!大紅榜貼在縣中門口,圍滿了焦急的考生和家長。我的名字赫然在列——總分356分,超過當年文科重點線16分!
但直到九月中旬,我的錄取通知書才遲遲到來。那天是留車公社的趕集日,我和父親走了整整一個半小時山路,趕到公社郵電所。當我通過長途電話聯系到學校傳達室,得知被江西師范學院中文系錄取時,心里真不是滋味。我填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學,是按校長的意見填的,遺憾的是北大未錄取,調劑到了江西師范學院。父親看出我的心思,用力拍拍我的肩膀:“老二,今后路還長著呢!只要爭志氣,前途一定是光明的。”
四十五年彈指一揮間,那段艱苦求學歲月卻如昨日般清晰。漏雨的舊宿舍、油墨清香的講義、恩師的教誨、后山樹下的傍晚景致,這一切都已成為我年少時最寶貴的財富。
高考改變了我這個農家子弟的命運,更讓我懂得了堅持與感恩的意義。那些照亮我青春歲月的明燈,至今仍在溫暖著我的人生旅程,提醒我不忘初心,砥礪前行。






 粵公網安備 44150202000069號
粵公網安備 44150202000069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