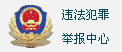○葉愛瓊

“一聲梧葉一聲秋,一點芭蕉一點愁。”秋風卷著落葉掠過肩頭,涼意起時,鄉愁便如陳年酒釀,在心底緩緩漾開。故園的輪廓、阿婆的笑容,伴著那抹熟悉的柿紅,又一次清晰浮現在眼前。
黃昏時分,獨自躑躅在螺河畔,一片枯黃的落葉輕輕棲在衣袖,攜著秋日獨有的清寂。極目遠眺,秋水悠悠接長天,暮色如墨暈染開來,鄉愁也隨之漫過心頭。此刻無童話爛漫,唯有對故鄉的牽念,在風里低低徘徊。
路過泰安橋頭,偶見小販車上堆疊的柿子,那一抹嫣紅似一把銅匙,瞬間開啟記憶的閘門,將我拉回故鄉那片魂牽夢縈的柿子園。記憶里的故鄉之秋,澄澈長天之下,潺潺溪流之旁,柿子園的嫣紅爛漫,是秋日里最動人的詩行。
上世紀八十年代的鄉村,物質尚不豐裕,但中秋前后的柿子園,卻是我童年最富足的樂園。自家的柿子園就在老屋對面的小山坡上,緊挨著一彎清澈的小河,不大的園子里,數十棵老柿樹錯落生長,虬曲的枝椏間藏著歲月的痕跡。每到初秋,柿子便褪去青澀,從微黃到橙黃,終至染上醉人的嫣紅。遠遠望去,像一盞盞玲瓏小燈籠,密密匝匝掛滿枝頭,壓彎了枝椏,把園子裝點得暖意融融。溪邊蘆葦已泛金黃,風過處沙沙作響,與枝頭柿子相映成趣,空氣中漫溢著泥土的芬芳與柿子的清甜,深吸一口,便是故鄉的味道。
“墻頭累累柿子黃,人家秋獲爭登場。”中秋佳節漸近,摘柿子成了家里的頭等大事。阿婆會提前幾日便備妥工具,找出那根伴她多年的長竹竿,竿頭綁著細竹篾編就的網兜——那是她親手所制,網眼大小恰到好處,總能穩穩接住摘下的柿子。我則拎著心愛的小竹籃,蹦蹦跳跳跟在她身后,像只雀躍的小尾巴,滿心期待著豐收的甜。
阿婆總先細細打量,專挑紅透軟熟的柿子下手。她舉起竹竿,手臂微收,小心翼翼將網兜套住果實,手腕輕輕一轉,只聽“噗”的一聲輕響,熟透的柿子便穩穩落網,清甜的果香隨風吹散。我連忙跑過去,小心地將柿子從網兜取出,放進鋪了柿葉的竹籃里,仿佛捧著稀世珍寶。偶爾有柿子不慎落在厚厚的落葉上,我撿起來用衣角一擦便要送進嘴里,卻被阿婆笑著攔住:“剛摘的要放放才更甜,聽話,回家給你挑最大最紅的。”
陽光透過疏枝,灑下斑駁光影,落在阿婆的銀發上,鍍上一層溫柔的光暈,也落在飽滿的柿子上,映得果肉愈發透亮。秋風拂過,樹葉沙沙,混著阿婆的溫柔叮囑與我的清脆笑聲,成了童年最動聽的交響。
落日余暉灑在鋪滿野菊花的小徑上,我們滿載而歸,竹籃里的柿子甜香一路飄蕩。回到家,阿婆便忙著分揀柿子,一邊擺置一邊說:“丫頭你看,這些個大、色紅、無瑕疵的,裝在好籃子里,給東頭王奶奶、西院張叔婆送去。都是老鄰居,好東西分著吃才更甜。”
我不解地問:“阿婆,最好的咱們自己留著不好嗎?”
阿婆停下活,抬手摸了摸我的頭,眼神溫柔又堅定:“傻丫頭,做人不能只想著自己。把好的給別人,人家歡喜,咱們心里也暖。你看這些帶點磕碰的,咱們自己吃,一樣甜呢。”說著,她拿起一顆略帶瑕疵的柿子,擦凈掰開,遞到我嘴邊。我咬下一口,甜汁瞬間充盈口腔,那甜味里,竟藏著一絲難以言喻的溫暖。
余下未熟的柿子,阿婆便做成軟糯的柿餅,那是冬日里最念想的零嘴。她先剪去柿蒂,清水洗凈,再用軟布擦干,握著特制削皮刀輕輕轉動——圓溜溜的柿子在她手中似有靈性,幾下便褪去外衣,果皮竟還能一圈圈連在一起,像件精巧的藝術品。阿婆將削好的柿子挨個擺進竹簸箕,每顆間都留著細縫:“這樣通風好,柿餅才甜潤不霉。”我學著她的樣子擺,卻總擺不整齊,還常碰掉柿子,阿婆從不責怪,只是笑著撿起重擺,再遞顆最圓潤的給我:“丫頭慢慢來,多練就好。”
陽光斜照在院子里,阿婆坐在小馬扎上,我蹲在她身旁,空氣中滿是柿子的清甜。她時不時翻動柿子,指尖拂過果實的動作,輕柔得像呵護嬰兒。“曬柿餅要講法子,清晨趁日出前搬出去沾露水,午時要翻面,黃昏得吹涼風,這樣才干得勻。”等柿子表皮微皺,阿婆便收進竹筐捂上幾日,“這樣才會長出白霜,那可是柿餅的精華呢。”每次說起這話,她眼里都亮晶晶的,藏著星光似的。
而那些熟透的柿子,除了分贈鄰里,阿婆總會在忙完后,挑出一顆最大最紅的,洗凈后輕輕剝開口,遞到我嘴邊:“嘗嘗,甜不?”我湊過去咬下一口,甜汁四溢,果肉綿軟,那甜味直沁心坎,滿是秋日的芬芳與阿婆的疼愛。那一刻,我便覺得自己是世上最幸福的孩子。
如今,阿婆早已化作天上星,故鄉的老屋在歲月里漸漸斑駁,溪邊的蘆葦枯了又榮,不知換了多少茬。那片柿子園,是否還如當年那般枝繁葉茂、柿紅滿枝?“露脆秋梨白,霜含柿子紅。”每到秋風起時,我總會想起那個柿園,想起阿婆慈祥的笑、溫暖的手掌,更想起她教我的道理——分享的甜,遠勝獨自品嘗的香。那抹柿紅,染紅了故鄉的秋,更鐫刻在我心底,成了鄉愁最暖的印記,成了對阿婆最綿長的思念。那份樸實的善意,也隨這記憶,伴我走過歲歲年年。






 粵公網安備 44150202000069號
粵公網安備 44150202000069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