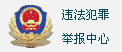○陳丹玉
青年干渠的歲月,被夕陽染成了一條流淌著金光的河。我站在這條熟悉的街道上,看著車水馬龍,聽著市井喧囂,恍惚間竟分不清今夕何夕。
青年干渠,這個名字如今成了一條街的稱謂。而在它的腳下,沉睡著的是一條來自青年水庫的灌溉渠。它曾經流過粉圍村、馬厝鋪、西門、大窟……最后匯入龍津河,像一條銀色的絲帶,串起了我對海城的記憶。
我的記憶,要從1984年說起。
那一年,我進縣城讀五年級,寄住在馬厝鋪的大姨家。那時的馬厝鋪與縣城之間,還橫亙著一條五六米寬的河渠。村民們進城,都要沿著渠壩走,過了西門那座叫“高橋”的青石板橋,才算真正進了城。
渠水清可見底,兩岸是望不到邊的田野。春天綠浪翻滾,夏天金濤涌動,到了秋冬,遍地都是新鮮的果蔬。從馬厝鋪到西門不過千米,渠邊的青石板上,每天清晨都聚滿了洗衣的婦人和姑娘。她們的歡笑聲伴著搓衣聲,在晨光中蕩開,驚起水面的蜻蜓。
渠壩很寬,上面開墾著一畦畦菜園。我常踏著晨露,蹦跳著走在壩上,聽渠水淙淙,看婦人們一邊洗衣一邊說笑。那些質樸的鄉音,至今還在我耳邊回響。
放學時分,我和西門的小伙伴們總是結伴小跑回家。我們最愛坐在青石板橋上,把腳浸在清涼的渠水里,晃動著,一邊漫不經心地聽著老人的彈唱,看著渠中戲水的孩童和給牛洗澡的農人。那時的陽光清澈透明,不帶一絲塵埃;那時的眼里,只有碧水清波、歡聲笑語。我們哪里懂得,這座光滑的青石板橋,連接的不僅是城郊與城里,更是一代人的青春與暮年。
1987年,我們一家在馬厝鋪租了房子。走出巷口就是河渠。從暮春到晚秋,這條河渠成了弟弟們的樂園。渠里有魚有蝦有蛤蜊,弟弟放學回家,書包一扔就約上小伙伴跳進渠里。大弟弟最會摸蛤蜊,半小時就能摸小半桶。母親用魚露腌制的蛤蜊,成了我們童年最香甜的回憶。
母親也在渠壩上開墾了一小塊菜園。弟弟們常從渠里爬上來,直接給菜園“施肥”,母親便趕緊澆水稀釋。那塊小小的菜園,四季輪回,青黃接替,滋養著我們清貧卻溫暖的歲月。
上世紀90年代初,改革開放的春風熱烈烈地吹到了縣城。南下打工的人潮涌來,縣城開始修建二環路。馬厝鋪前的河渠依然靜靜流淌,但東邊路口的河渠已經被鋼筋水泥覆蓋。我家在渠邊買了地,蓋起平房,終于有了屬于自己的家。
風氣的轉變,是從二環路的車馬聲越來越稠密開始的。后來,縣政府真個兒西遷了過來,馬厝鋪就像忽然被推到了舞臺中央,身價眼見著不一樣了。父親在信里說,鄉親們如今見面聊的,都是誰家又起了新樓。他們說“種房子”,比種莊稼還要上心。等我1995年畢業,拖著行李回到這片土地時,竟像個外鄉人一般,在縱橫交錯的新巷弄里輾轉尋覓——我家那間小平房,早已被一片陌生的樓群海洋吞噬得不見蹤影。
隨著外來人口的增多,生活垃圾也多了起來。河渠邊不知不覺成了垃圾堆。昔日清澈照人的渠水,變得渾濁不堪;曾經瓜果飄香的渠壩,臭氣熏天。每逢下雨刮風,住在附近的居民苦不堪言。那條承載著我們無數美好記憶的河渠,在時代的洪流中黯然失色。
直到本世紀初,“創文創衛”的春風吹遍大江南北。2010年前后,青年干渠應運而生。那條來自青年水庫的河渠,終于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被永久地封蓋在鋼筋水泥之下。取而代之的,是一條整潔繁華的街道。
如今的青年干渠,早已不是當年的模樣。寬闊的水泥路兩側,商鋪林立,燈火通明。以前泥濘的渠壩、曾經垃圾成堆的河邊,變成了平整的人行道。
清晨,各種小食店和商鋪迎著晨曦開門;午后,各種地攤一字排開;夜晚,路燈明亮如晝,咖啡店、夜宵店徹夜忙碌……垃圾分類回收,再也聞不到刺鼻的氣味;二環路四通八達,網約車開到了家門口。
可我在叩問心里,當那條具體的、有溫度、有聲響的河渠被封存,我的一部分關于這片土地的印記,也隨之被埋葬了。
昨夜夢里,我又回到了那條清凌凌的河渠邊。渠水還是那么清澈,婦人們還在青石板上洗衣說笑,弟弟們還在渠中摸蛤蜊,老樹下還有老人在拉二胡。我醒來時,窗外已是晨曦微露,青年干渠又開始了一天的繁忙。
我知道,那條河渠從未真正消失。它只是換了一種方式,流淌在街坊鄰里便捷的生活里。這或許就是生長必須付出的代價——用一條清凌凌的、具象的河,換一條更寬闊的、名為“生活”的河。
如今,每每回家,我依然會在夕陽西下時漫步青年干渠,看著來來往往的笑臉,聽著此起彼伏的歡笑聲。我也欣然接受這份時代贈與的精美禮物,而心底卻終有一角,無法與它肝膽相照。






 粵公網安備 44150202000069號
粵公網安備 44150202000069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