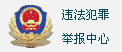○陳丹玉
假日的鄉愁,總是從舌尖開始漫溢的。
假日里,約上老姐,和三五舊友坐在家鄉的飯館里,杯盞交錯間,說著些閑散的話。服務員笑盈盈端上一大盆熱騰騰的吃食,說是贈送的特色小吃——鼎溜粿。名字一出口,我的心便像被什么東西輕輕撞了一下。滿桌的佳肴瞬間失了顏色,我的目光,我的魂兒,全都落在了那一盆氤氳著蒸汽的白圈圈里。
這鼎溜粿啊,是我們這代人童年里最扎實、最溫暖的念想。在那個物質尚且匱乏的年代,它是農閑時節,母親們變出的最美食物。
印象里,晚稻歸倉之后,新米碾出來了,帶著陽光和土地的氣息。女人們便會舀出最濕潤細膩的米粉,在巨大的瓦盆里,不緊不慢地調起米漿。水是河溪的水,也帶著陽光和土地的味道。灶膛里,干透的柴火燃得噼啪作響,大鐵鍋里的水咕嘟咕嘟地滾著,冒著水汽。這時,母親便舀起一碗米漿,沿著滾燙的鍋邊,手腕那么靈巧地一轉、一泅,米漿便聽話地粘在了鍋壁上。只需幾秒鐘,那片薄薄的米漿便由乳白變得透明,邊緣微微卷起,再用鍋鏟輕輕一鏟,它便像一只乖巧的白玉泥鰍,“溜”地一下滑進滾水中。如此一圈,又一圈,直到所有米漿都化作滿鍋游弋的、軟滑的卷兒。最后,撒上一把提前炒香的蘿卜干、花生米,再點綴些翠綠的蔥段,只需一點鹽,一鍋清白、爽滑的鼎溜粿便成了。它能撫慰轆轆饑腸,更是農家人“拍斗四”(聚餐)時,最能烘托氣氛的樸實佳肴。
如今,飯店的鼎溜粿,用料更為講究,花生米油亮,蔥段和芹菜段碧綠,漂在清湯上,煞是好看。可我看著它,眼前浮現的,卻不是這精致的碗盆,而是老姐家那間矮矮的土屋,和阿姨那一聲聲帶著泥土芬芳的呼喚:“阿玉,我的憨囡……”
那是1985年的秋天了。我和老姐,像兩顆不起眼的種子,幸運地落在了彭湃中學這片沃土。我們是班里僅有的兩個穿著帶補丁衣服的農村妞,彼此的膽怯和淳樸,讓我們迅速靠近,成了最要好的姐妹。我家在城郊平原,田地肥沃,出產好稻米;老姐家在蓮花山路邊,靠山吃山,養得一群好雞鴨。于是我們便有了一個甜蜜的約定:我帶來大米換成飯票,她帶來家里腌的咸菜和鴨蛋。
每天的午飯時光,我們最快樂。姐妹倆躲在教室的角落,或坐在大榕樹的濃蔭下,共吃一盒白米飯,就著咸鴨蛋和咸菜,那滋味比任何山珍海味都來得悠長。我們聊我家的稻谷,聊她家的鵝鴨,更密謀著周末要叫上玩得好的彬和林,一起去我家幫忙割稻,去她家后山摘那漫山遍野的野果子。
而我最期待的,便是去老姐家。每次剛走到那山凹邊,還沒瞧見那土屋的影子,阿姨那親切的聲音便會先傳過來。她總會放下手里的活計,快步走出來,用那雙因常年勞作而粗糙卻十分溫暖的手,緊緊拉住我,連連叫著:“阿玉,阿玉,我的憨囡(海豐話,傻妞的意思),快坐下歇歇,阿姨給你做鼎溜粿吃!”
那時,老姐家的屋子低矮,卻充滿了生機。我和老姐把那個用塑料繩編成的書包往桌上一扔,就像兩只出籠的小鳥,飛到屋后的小山坡上。我們對著空曠的山谷,大聲唱起音樂老師新教的歌,是費翔的《故鄉的云》。“天邊飄過故鄉的云,它不停地向我召喚……”我們的歌聲帶著少女的稚嫩和羞澀,常常還沒唱到“歸來吧,歸來喲”,山下阿姨那拖長了調子的呼喚便悠悠地傳了上來:“阿紅——阿玉——我的兩個憨囡哎——回來吧,鼎溜粿好啦——”這時,我和老姐便會相視一笑,手拉著手,像兩個雀躍的陀螺,大笑著從山坡上輕盈地“滾”下來。
阿姨做的鼎溜粿,是世上獨一無二的。那一卷兒一卷兒的米粿,軟滑中帶著韌勁,把阿姨所有的歡悅和疼愛都卷在了里面。她總是給我們盛上滿滿一大碗,湯水不多,料卻十足。最靈魂的是那勺她自家種、自家炒的花生米,油香酥脆,配上從門口菜畦里隨手拔來的小蔥和芹菜,那個香氣呀,能一下子鉆進人的心窩里。我總會吃得頭也不抬,阿姨就坐在一旁,笑瞇瞇地看著,不時用手捋捋我跑亂的頭發,念叨著:“慢點吃,慢點吃,憨囡,鍋里還有呢。”
三年的初中時光,就在這鼎溜粿的香氣里,溫柔地溜走了。每一個周末,每一個假期,尤其是漫長的暑假,老姐家就是我的第二個家。我們一起摘多尼(山稔子),把嘴唇吃得紫黑;一起在山澗里洗腳,任由小魚兒啄著腳丫。而這一切快樂的終點,總是阿姨那一碗暖心的鼎溜粿,和那一聲聲百聽不厭的“憨囡”。
后來,我上了高中,老姐也開始了半工半讀的師范生活。日子仿佛一下子被拉長了,也變快了。老姐家蓋起了明亮的紅磚瓦房,哥哥們成了家,阿姨也漸漸不再做鼎溜粿了。再去時,她會給我煮一大鍋香噴噴的米飯,煎上好幾個黃澄澄的土雞蛋,一個勁地往我碗里夾:“阿玉,多吃點,多吃點,家里的雞蛋好,不賣了,都留給你們吃。”那語氣里的疼愛,一點都沒變。
再后來,我上了大學,參加了工作,到了他鄉。每次去看望阿姨,她總會提前擂好一缽芝麻花生咸茶,那濃香撲鼻的味道,一如當年的鼎溜粿。她依然坐在我身邊,不停地給我添上一碗又一碗,看著我喝得香甜,她臉上的皺紋便舒展開來,依然像喚著那個從未長大的小女孩一樣,喃喃道:“阿玉,我的憨囡。”
我曾想,究竟是阿姨的鼎溜粿溫馨了我和老姐的豆蔻年華,還是我們這兩個“憨囡”的歡聲笑語,柔潤了阿姨那原本貧寒而艱辛的歲月呢?或許,愛與陪伴,從來都是相互滋養的吧。
2015年,阿姨因腦萎縮臥床,漸漸忘記了身邊的親人,忘記了流轉的光陰。那個暑假,我回去看望她。我和老姐輕輕地走到床邊,俯下身,同時喚了一聲“阿姨”。一片寂靜中,阿姨渾濁的眼睛似乎動了一下,嘴唇囁嚅著,居然清晰地喃喃出:“阿玉……阿玉啊……”
那一刻,我再也忍不住,緊緊抱住身邊同樣淚流滿面的老姐。原來,有些記憶,會被病痛帶走,但有些刻在生命里的回聲,永遠不會消失。
歲月無聲,靜默流淌。如今,家家戶戶都用上了燃氣灶,那口能做出鼎溜粿的大鐵鍋,早已退出了生活的舞臺。鼎溜粿,成了餐館里一道懷舊的風景。感謝那些充滿人情味的家鄉老板,將這份傳統的滋味,作為禮物送給遠道而歸的游子。
我舀起一勺眼前的鼎溜粿,放入口中。米香依舊,花生依舊。只是,我咀嚼出的,更是那段遠去的時光,是阿姨那雙溫暖的手,和那一聲穿越了數十年光陰、至今仍在耳邊回響的——
“阿玉,我的憨囡,回來吃鼎溜粿啦……”






 粵公網安備 44150202000069號
粵公網安備 44150202000069號